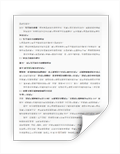建筑师不是演员。社会期待召唤明星建筑师,一定是希望他们承担更多的东西,希望他们手中的利刃能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摆在聚光灯底下承受香火。客观地说,在当代中国,成为一位明星建筑师是相对容易的。以中国建筑有限的物质和精神准备,由舆论所设定的成就点非常之低,稍一努力就掌声一片。有人甚至认为:明星建筑师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服务于大量建设的 。对此,旁观者清,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执行总监Martha Thorne女士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代中国建筑与国际一流建筑的设计质量还是存在差距的,这种差距已经不再体现在建筑的规模和技术层面(奥运世博项目都证明了这一点),而真正存在差距的是建筑的思哲层面,即如何让建筑具备更加深邃的精神品质,或者说,如何把握对建筑本源的批判性思考和空间上的创造,让建筑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应该是下一阶段中国建筑师的努力方向。”久久建筑网--中国建筑行业门户网站
在精神追求方面,回顾中国建筑界历时并非久远的探索历程,其中的转变耐人寻味。一方面,早年心智初开之际轻易给自己和别人贴上去的标签如今被偷偷撕了下来;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艰辛的工作、累积的声望和小康之后五色斑斓的世界都让意志逐渐消磨,所谓“新知不益,物诱日多”。 中国这一代有追求的建筑师的“扎根”过程,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以同情的角度观之,“这也是一种扎根,虽然充满无奈,但至少表现了一种追求的信念和坚韧。” 而圈外的批评者显然没有这般温柔,“一般知识阶层”对明星建筑师充满了期待,大众的造神运动,并非旨在培养几个国内媒体供奉的偶像——对外理屈词穷,对内附庸风雅。史建追溯历史,找到了理想主义的灭点:“张永和在《第三种态度》中表达了‘批判地参与’,以及‘立场的根本性,策略的不定性’等观点,并且提出了要以十年纪念为契机,实现‘非常建筑’从一个个人化色彩浓厚的建筑师工作室向组织严密的建筑师事务所的转型,而‘非常建筑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业务上国际化的建筑事务所’。在这些表述中,介入现实的‘入世’(市场经济)欲望的强烈,已经遮没了‘实验’性,而非常建筑在此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这一文章发表于2003年的《建筑师》杂志的纪念专辑,“十年”这个常数在此又一次映入眼帘。久久建筑网--中国建筑行业门户网站
一个系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边缘批评性力量和核心建制化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中国建筑实验精神(先锋性)在十年中整体退潮,却没有新一代的有生力量填补空白,这是其中的原委到底是什么?史建将“实验精神”消退的原因归结为语境的转换——它所要对抗的秩序“消失”了,它开始全面介入主流社会,它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世界。亦即,一旦幡然醒悟,明白敌人不可战胜,就选择了接受招安。 眼前的秩序还是那个秩序,只是实验建筑师们不再愤怒。朱涛却认为,所谓第一代实验建筑师的假想敌和武器都是靠不住的:“其中一些觉得只有靠来更生猛的,更狂怪的,非要摆出一个强奸context的姿态,才对得起‘前卫’、‘激进’、‘能量’这些字眼儿。另一些觉得坚持做纯净点的形式,把墙刷白,加点木百叶,就算文化上的抵抗,或‘批判’了——这些恐怕都还是糊弄,都还是太过简单的花拳绣腿。”归根到底,建筑师内力不足、小富即安,是批判性失落的根源。这些态度,都表明了舆论对这个“无梦”的十年的失望。